1785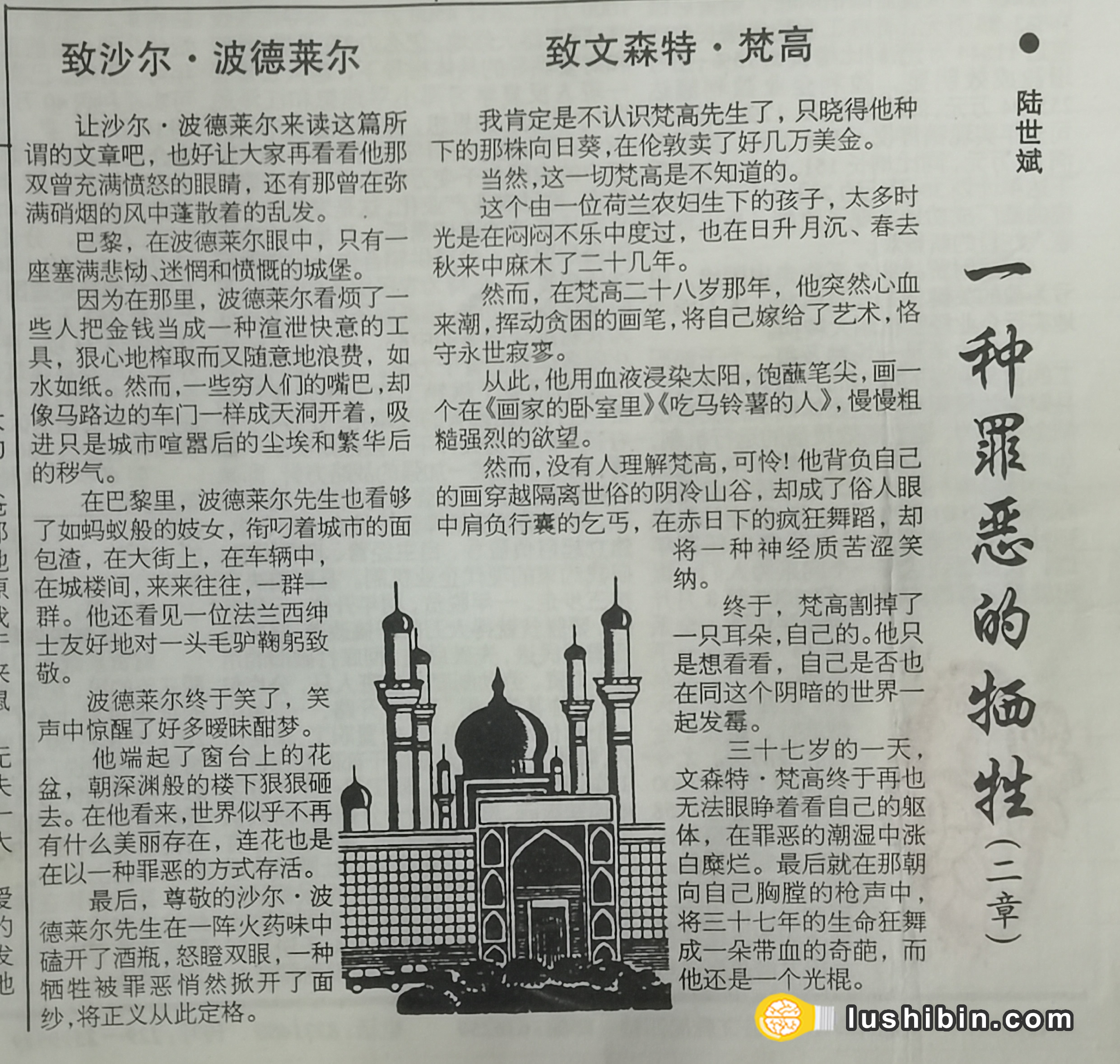
致沙尔·波德莱尔
让沙尔·波德莱尔来读这篇所谓的文章吧,也好让大家再看看他那双曾充满愤怒的眼睛,还有那曾在弥漫硝烟的风中蓬散着的乱发。
巴黎,在沙尔·波德莱尔的眼中,只是一座充满悲恸、迷惘和愤慨的城堡。
因为在那里,沙尔·波德莱尔看烦了一些人把金钱当成一种宣泄快意的工具,狠心地榨取而又随意的浪费,如水如纸。然而,一些穷人们的嘴巴,却像马路边的车门一样成天洞开着,吸进的只是城市喧嚣后的尘埃和繁华后的秽气。
在巴黎里,沙尔·波德莱尔先生也看够了如蚂蚁般的妓女,衔叼着城市的面包渣,在大街上,在车辆中,在城楼间,来来往往,一群一群。他还看见一位法兰西绅士友好地向一头毛驴鞠躬致敬。
沙尔·波德莱尔终于笑了,笑声中惊醒了好多暧昧和酣梦。
他托起窗台上的花盆,朝深渊般的楼下狠狠砸去。在他看来,世界似乎不再有什么美丽存在,连花也是在以一种罪恶的方式存活着。
最后,尊敬的沙尔·波德莱尔先生在一阵火药味中磕开了酒瓶,怒瞪双眼,一种牺牲被罪恶悄然揭开了面纱,将正义从此定格。
致文森特·梵高
我肯定是不认识梵高先生了,只晓得他种下的那株向日葵,在伦敦卖了好几万美金。
当然,这一切梵高也是不知道的。
这个由一位荷兰农妇生下的儿子,大多时光是在闷闷不乐中度过,也在日升月沉、春去秋来中麻木了二十几年。
然而,在梵高二十八岁那年,他突然心血来潮,挥动贫困的画笔,将自己嫁给了艺术,恪守永世寂寥。
从此,他用血液浸染太阳,饱蘸笔尖,画一个在《画家的卧室里》《吃马铃薯的人》,慢慢粗糙强烈的欲望。
然而,没有人理解梵高,可怜!他背负自己的画穿越隔离世俗的阴冷山谷,却成了俗人眼中肩负行囊的乞丐;在烈日下的疯狂舞蹈,却将一种神经质苦涩笑纳。
梵高割掉了一只耳朵,自己的。他只是想看看,自己是否也在同这个阴冷的世界一起发霉。
三十七岁的一天,梵高终于再也无法眼睁着看自己的躯体,在罪恶的潮湿中涨白糜烂。最后就在那朝向自己胸膛的枪声中,将三十七岁的生命狂舞成一朵带血的奇葩,而他还是一个光棍。
1999年6月写于开江长田
2001年3月刊于《开江作家》第11期
638801168413581380